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網發表瑞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文章表示,去產能終于破冰,反映政府在“穩增長”巨大壓力下,主動出擊,大刀闊斧推進改革的表現。然而“既要產能退出,又要盡可能重組,少破產”,“讓大量職工工作不丟”的領導人表態也顯示了對待去產能工作的矛盾心態和難度,表明深處于產能過剩的困境之下,去產能工作已無可回避,不得不為之中亦透露出有些許無奈之意。
產能過剩一直是近年來中國產業發展的“痼疾”。不僅困擾著鋼鐵、水泥、電解鋁、玻璃等傳統行業,而且太陽能、風能等新興產業也難逃厄運。產能過剩行業整體虧損,機構繁雜,人員工資難以保證,困境之下,常年來依靠銀行貸款不斷展新,地方財政持續補貼度日,整體而言拖累中國經濟。
產能過剩風險之所以值得重視還在于來自國際經驗的警示。日本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爆發的房地產泡沫與其后三十余年的經濟衰退令人不寒而栗。實際上,對比當前中國與日本危機之前的情形,不難發現,其實已有不少相似之處,如經濟增長放緩、貨幣政策效用遞減、貨幣升值削弱出口競爭力等等。同時,危機爆發前的日本經濟同樣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局面,大量僵尸企業占據社會資源,避免創造性破壞,長此以往,風險積聚導致最后以危機形勢爆發,最終陷入流動性陷阱,亦值得中國引以為戒。
如何去產能是個難題,當前中國決策層開出的藥方主要包括:嚴格控制增量;盡可能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完善財政、金融等支持政策,做好職工安置;通過債轉股能降低杠桿率和提升再融資能力,并能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在深層次上實現產能過剩行業的重組。
文章稱,期待是好的,但可以預見,上述措施在落實中,仍將面臨難題。比如,當前決策層去產能的思路體現了一種平衡思維,既要去產能,又要保就業,但也面臨理想狀態推進的不確定性。試想在市場條件下,如果企業財務狀況若已達到破產境地,反而要求兼并重組,具體操作是由市場還是行政手段主導呢?由誰來出面?倘若任務又會落到國企肩上,是否有違于國企改革初衷?
同樣,如何做好職工安置,避免大規模社會問題出現也至關重要。然而,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今年3月政協會議分組討論時也提到,做好職工安置問題離不開養老、醫療保障體系的改革。但是,當前來看,上述改革進展仍然緩慢,現收現付在保障體系所占的比例仍然相當高,現在的人還承擔著過去中老職工的養老保障負擔。養老金賬戶可攜帶性不足,也是職工轉崗再就業的體制性障礙。
此外,備受期待的債轉股,能否對于去杠桿、化解產能起到很好作用?理論上可以,但在國有企業改革推遲,企業經營行為無法實現市場化運作的當下,如何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進行公司決策仍然是個難題。試想進駐被整合的國有企業的懂事會成員,在現有體制下,行政級別很可能低于需要紓困的企業管理者,這種情況下,如何履行其對公司治理監督的職責效果存疑。
如此看來,與市場化國家去產能有所不同,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化解絕不能僅就去產能而“去產能”,要從制度性、體制性原因出發,配合以行政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價格改革、金融與財稅改革等多項措施協調推進,才能達到標本兼治,從根本上化解產能過剩危機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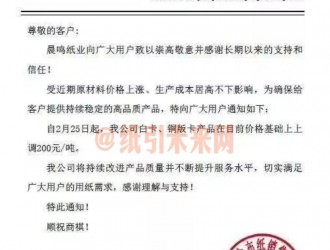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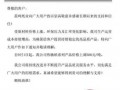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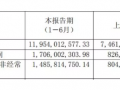







 紙友
紙友
 行情
行情
 訂單
訂單
 廣告
廣告
 找貨
找貨
 簽到
簽到

 關注
關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