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民營書業推動了市場上80%以上的暢銷書和95%以上的渠道零售教輔的出版。這些民營書業公司的掌舵人大都具有出版人的夢想、激情和文化擔當精神,具有強烈的推動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與現代文化“走出去”的情懷。那些在書業摸爬滾打了10年乃至20年以上的公司積淀了一定的策劃創意人才,高效、富有市場感的流程與機制和獨特的企業文化,一部分民營出版公司還建成了自己的辦公大樓、物流基地甚至文化產業園,成為所在省市文化產業的領軍型企業。
包含出版業在內的服務業發展的瓶頸不在需求,而在供給,“十三五”期間,服務業一定會加速開放,在醫療教育養老健康金融等領域對社會資本和外國資本擴大開放。在民營書業業已成為中國出版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的新情境下,試點或逐步對民營開放出版權的時機與條件是成熟的。畢竟,全球化的文化競爭是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競爭,在出版行業不應演繹為是我國國有出版企業與其他國家的全民出版企業的競爭。如何改變國內缺少文化(出版)航母,缺少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化(出版)品牌這樣的現狀?我覺得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地給予民營書業合法出版資格,在確保國家文化安全和控制力的前提下,大力倡導民營出版機構與出版社的資本合作、逐步降低出版業的資本準入門檻和對股本比例限制(從絕對控股到相對控股),充分調動社會資本發力出版產業、引領出版業轉型的積極性,充分釋放民營資本的文化創造力,應該是一個迫切的選項。
民營書業面對的現實的瓶頸之一是:民營策劃、發行公司需要與資本市場對接,需要成為公眾性企業,但它們只是流通性企業,只能從出版社購進圖書,然后賣出去,紙款、印刷款等生產環節的重要成本無法合法地體現在自己的賬面上。是否由出版社支付印刷費、紙款、稿費等,仍然被作為是正常的合作出版還是“買賣書號”的重要認定標志。在已經上市或處于上市準備期的民營公司那里,出版社、印刷廠(紙廠)、策劃發行公司之間的結算環節無可規避地進入了人為架構的“體內循環”狀態;而部分有一定規模、尚無上市計劃的民營公司,前幾年則通過當地政府協調或當地稅務部門出于集聚稅源等的考量,認可了其與印刷廠(紙廠)間的直接結算。如能賦予有一定規模的民營策劃公司以租型權,由出版社、出版物策劃與制作公司及印刷廠(紙廠)之間自行商定民營公司擁有完全知識產權的產品的印刷生產環節的業務流程,自愿約定費用支付主體,讓民營公司由流通性企業合法地成為制造型企業,則既沒有突破出版社在出版物內容導向與質量的控制權,又將極大釋放民營公司的創造力量,有力助推民營公司做大、做強。
瓶頸之二是:由于中級及以上編輯的職業資格考試不對民營公司從業人員直接開放,導致在教輔出版物內容與編校質量的責任主體錯置,民營公司的內容生產與編輯人員沒有其他服務性、技術性、創新型行業那樣具有一條通暢的、社會化的職稱晉升通道,無法形成職業的歸屬感與自豪感,隊伍建設前景堪憂。
有一定歷史與規模的民營公司無疑都擁有一群資深的編輯,他們大都具有十年以上的從業經歷,在選題策劃、內容質量打磨、編校質量提升等方面,擔負著重大的責任并起著核心的作用。但和出版社年輕的同行及進入出版社的曾經的部下、徒弟相比,他們既不可能通過努力擁有中級以上的編輯資質,更沒有“責任編輯”的署名權;春雨集團建有民營公司較早的黨總支,四個支部,110多位黨員,中共黨員無疑是本科生、研究生中的佼佼者,但若干年后他們吃驚地發現,和自己進入出版社的同學相比,他們這些在民營公司從事編輯工作的黨員員工連參加中級編輯職業資質考試的權利都沒有!
在出版社與民營公司的出版合作中,前期的選題策劃、組稿、編校、審讀,后期的品牌維護、售后服務等,都是由民營公司的編輯完成的。比如,春雨集團積20余年教輔運作的經驗、教訓及數字化轉型的需要,發布了“教育內容的生產、加工、存儲與發布流程”,在內容生產的各個環節都制定了標準與流程,實現了教育內容的一次生產、適度加工、多元發布。教材進入“一綱多本”階段及教育需求的差異化,導致市場品種激增,大部分出版社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擁有100、甚至200以上的編輯力量來完成做題、驗題等各環節的編校與審讀工作,建立嚴格意義上閉環的內容質量保障體系和編校質量保障體系。品種的激增,加上教輔出版時間集中,將書稿的內容與編校質量的責任落實在出版社有限的編輯身上,顯然是不現實的。至少在教輔出版領域,出版社的編輯人員能夠完成的基本上只是選題的申報、終審終校、開發印單、樣書繳存等事務性工作。
教師資質、律師資質、注冊會計師……服務業的各項資格考試都已經向全社會開放了,為什么作為文化產業的一個部分的出版業的中級以上編輯資格考試卻只有出版社人員才能參加? 改革開放30多年,民營書企的編輯不乏有進入國有出版社或或中途離開出版業的,但更有一批10年、20年以上的從業者,他們將青春年華奉獻給了中國的民營出版業,擔負著出版物全部的質量責任甚至市場風險等,但他們卻一直沒有執業資格,沒有職稱,其心理的挫折無疑是巨大的。這個行業怎么能留住那些有理想、有抱負、有才干的精英人才,他們的價值、成長性、職業自豪感通過什么來體現?——這已經不是與薪資、待遇相關的問題了。
打破這一瓶頸的建議是:對與出版社進行出版合作的民營公司的資質進行梳理并設立必要的門檻,賦予有一定品牌、規模及專業編輯團隊的民營公司與出版社進行出版合作的資格,明確民營公司作為與出版社合作的圖書的內容質量與編校質量的責任主體,建立必要的考核與獎懲體系;同時,將中級及中級以上編輯資質考試向民營企業的從業人員直接開放,對獲得初級、中級編輯資格的圖書制作公司的人員,允許在制作與出版分離的圖書中以第二責任編輯、助理編輯或責任校對名義署名,從而為民營書業內容生產的從業者打通職業生涯發展通道,讓這個行業能夠吸納更多有創意、有才華、有責任心與奉獻精神的精英人才加盟。出版行政主管部門也可加強對本行政區域內圖書制作與出版分開相關活動的日常監督管理,指導圖書制作公司編輯人員參加出版方面教育培訓和職業資格考試、職稱評審等。
目前,民營書業企業與出版社之間的合作絕大部分是按照現行的出版管理體制進行的,制作與出版一直是有序地分開的。如果有區別,那就是隨著民營力量的成長,出版合作的內容提供方由個人更多地轉變為有一定規模的機構。如能從制作與出版分開的角度,首先突破上述兩大現實瓶頸,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文化企業規范有序參與圖書制作和出版分開改革,使得國有出版社、民營制作公司的功能、職責進一步明確,無疑能夠規范現行出版合作形態,提升合作運營效率,進一步釋放民營機構內容生產的創造力,以推動出版業在“十三五”期間獲得健康繁榮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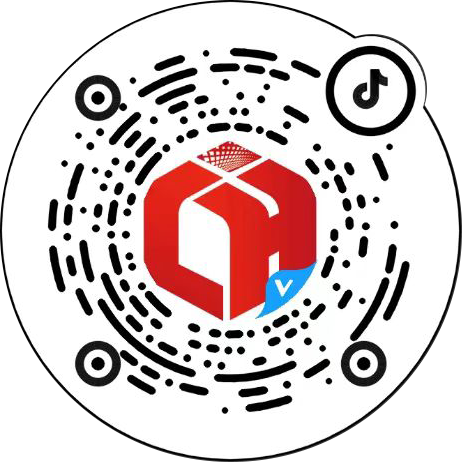




















 行情
行情
 訂單
訂單
 廣告
廣告
 我要
我要
 簽到
簽到

 關注
關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粵公網安備 44011202002240號
粵公網安備 44011202002240號